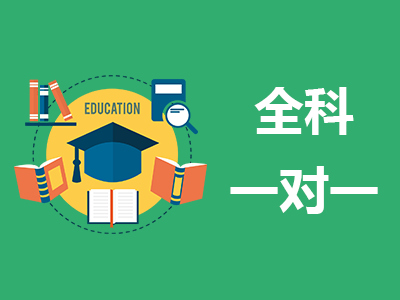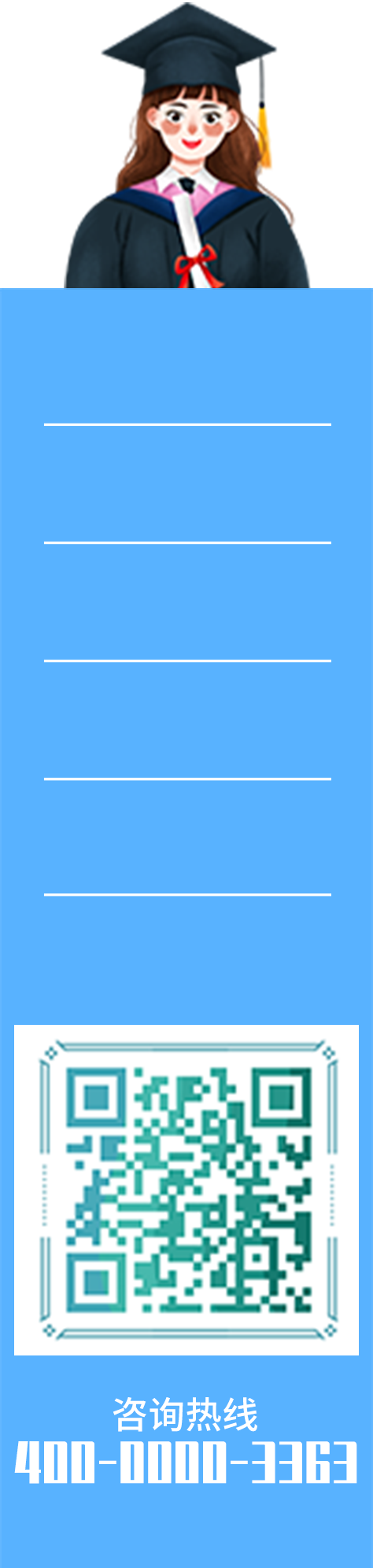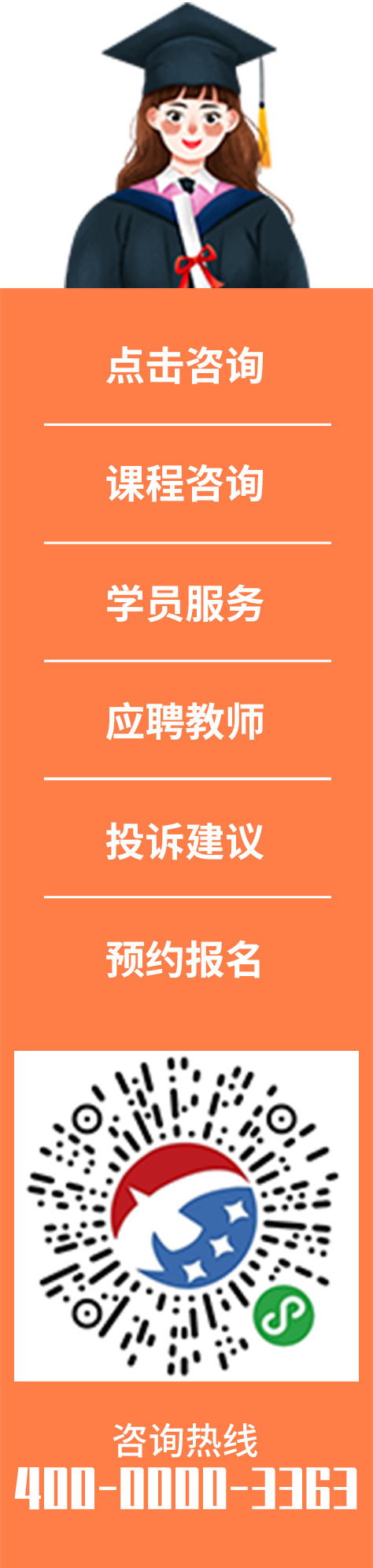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拥有特权,享有特殊的生活方式。历来学术界对于“士绅”的定义有各种不同看法,与之相近的概念有“乡绅”、“绅士”等。明清时期,“乡绅”主要是指居乡或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而“绅士”一词在明代主要还是分指“乡绅”与“士人”,到晚清则演变为对所有“绅衿”的尊称和泛称。“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为方便起见,在下面的叙述中,“绅士”与“士绅”往往互用。
对明清士绅的研究,日本起步较早,对明清绅士的考察范围逐渐从宏观走向微观。其为学旨趣大体相同,力图说明绅士的本质,并进而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当日本掀起绅士研究热时,欧美汉学界也不甘寂寞,陆续推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尤以张仲礼、萧公权、何炳棣、费正清等人的研究成果影响力大。国内绅士研究虽然相对薄弱,但起步并不晚,早在20世纪40年代,吴晗、费孝通、潘光旦等人已着重围绕绅士的流动、绅权与皇权的关系探讨了这一问题。近年来,王先明、马敏、贺跃夫、郑振满等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分量。
在明清绅士的构成方面,张仲礼把中国绅士分为上层集团与下层集团。许多通过初级考试的生员、捐监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较低功名的人都属于下层集团。上层集团则由学衔较高的以及拥有官职的绅士组成。同时,张仲礼还根据绅士身份获得的途径分绅士为“正途”和“异途”两种。“正途”就是考试途径,“异途”则是捐纳途径。(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在整个绅士阶层中,下层绅士所占比例远大于上层绅士,并且上层绅士也来自下层绅士。
明清绅士享有许多特权,这使他们不同于社会的其他阶层。绅士一般被视为与地方官平起平坐,可自由见官。在礼仪方面,绅士同官吏一样,其特殊的称呼、饰物、顶戴、服装都不同于平民百姓。在家族祭祖时,身为绅士的家族成员往往被推崇为族中领袖人物;在地方上的各种节庆和典礼中绅士也承担了特别的作用。在法律上,绅士所享有的势力和威望也得到保护。在经济上,绅士也享有免缴某些赋税、徭役以及享有例银或其他津贴的特权。(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32~40页。)
在社会职责方面,绅士“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由于大量地方事务的实际管理都操纵在绅士手中,因而绅士往往充当了政府官员与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在经济收入方面,绅士身份是富贵利禄的保证。绅士们通常能够有效地开展和参与某些取得报酬和争得收入的活动,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张仲礼在他的另一本研究绅士的书《中国绅士的收入》中,详细地研究了中国绅士的收入问题。他指出:“在19世纪的中国,绅士最重要的收入来自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补偿”,具体包括担任官职、处理地方事务、充当幕僚、教学、当医生、帮人撰写等。另外,“绅士从他们拥有的财产中获得的收入也是很重要的。此种收入主要有两类:得自土地的收入和来自经商的收入”。在经商办企业中,由于“绅士在积累资本和影响官府两个方面都处在最有利的地位,因此能最成功地经营大企业的人是绅士”(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
由于绅士拥有诸多特权,因而在前近代社会中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尤其在社会变革和社会动荡时期,其地位和作用更为显著。
总之士绅问题,对前近代士绅的研究,日本起步较早,考察范围逐渐从宏观走向微观,力图说明绅士的本质,并进而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欧美汉学界也陆续推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尤以张仲礼、萧公权、何炳棣、费正清等人的研究成果影响力大。国内绅士研究虽然相对薄弱,但起步并不晚,早在20世纪40年代,吴晗、费孝通、潘光旦等人已着重围绕绅士的流动、绅权与皇权的关系探讨了这一问题。近年来,马敏、王先明、贺跃夫、郑振满等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分量。这些研究表明,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精英的兴起,对基层组织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起了重要作用,中央与地方权力发生转移,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政府职能部分转移至民间社会。
【课程顾问】任老师
【电话】13611267718
【微信号码】13611267718
【QQ号码】1558532534